【23xiu.com-爱上秀-教育信息门户网】
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逐渐沦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失能老人尤甚。失能老人在老年研究文献中大量存在,通常认为失能老人指的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
国际上通常依据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DLs)对其进行评定,ADLs根据障碍的严重程度在《国际残损、残疾和残障分类》框架下被普遍用来对个人进行分类。ADL的测量始于Katz,他建立的原始量表包括六项活动:洗澡、穿衣、上厕所、起床和从椅子上站起来、进食和禁欲。尽管禁欲在老年人的功能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不因生理限制而存在已经被接受,因此不再包含在ADL障碍评估中。后来又出现了巴氏量表,Lawton和Brody制定了日常生活能力量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由躯体生活自理量表(PSMS)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量表(IADL)组成,PSMS是对自理必需的生活维持活动的测量,其所包含的项目和Katz的ADL指数的内容是相似的,包括ADL分为14项,上厕所、进食、穿衣、梳洗、散步和洗澡;IADL测量的是更复杂水平的能力,对于个人独立生活是必要的,包括打电话、购物、准备食物、做家务、洗衣服、使用交通、服药和管理财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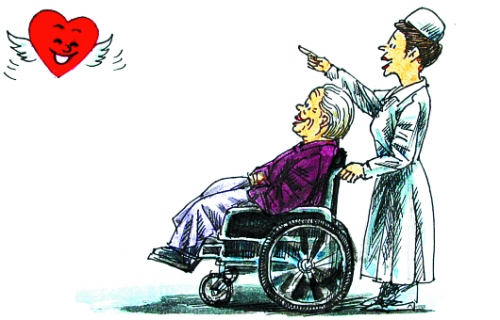
ADL的测量上存在着显著的概念和方法论问题。第一,ADL所包含的活动的数量不一致。我们根据个人是否能够实施某项活动来确定其依赖程度,那么越多的活动被包含在量表中,那么个人被认为依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出于研究的需要,会在Katz六项基本内容的基础上上下浮动,增加或减少几项。第二,在具体调查活动中,调查差异要远小于评估方式的差异。问题措辞和允许回答的差异,和测量误差一样,可以解释最后不同研究间和研究内的明显差异。ADLs中最经常被使用的障碍定义是依赖,经常依赖于另一个人,就其本身而言依赖于情境因素比如生活安排。ADL问题的实际措辞是重要的,从假设的“你能”到试图测量实际表现“你是”而变化。在临床环境中ADLs的假设时态很明显更为合适,但是ADL测量现在被广泛使用于社区居住的老人间,要求测量实际表现。最后,执行一项活动的困难已经被作为无能力执行任务的一种替代,在实际测量中不能够简单归类。
同样,IADL也缺乏一个一致认可的清晰的操作性定义,IADL测量的内容经常反映了特定的文化关怀。例如,英国测量往往包括沏一杯茶的能力。IADL量表的内容也反映出文化差异,也可能有性别偏见。IADL量表被认为过分强调了通常由女性执行的任务,因此过高估计了男性的依赖性。Gillian Ward等人曾对现存的IADL评估所使用的项目进行内容分析,他们比较了测量ADL的不同量表所选择项目内容的频率,比如做饭被测量的次数最多,23次,随后是做家务,社交,乘坐交通工具,洗衣服,购物,管理财务,打电话,工作和服药,服药只有2次。由此可见,在项目的选择上有着较强的个人意志在里面。
IADL还有着明显的类别差异。加拿大职业活动量表(COPM)是一种个人测量,允许病人或研究对象来确定那些他们视为问题的领域的职业表现,以至于他们可以关注结果测量;所以分数是个人化的不仅针对男女,而是每个人。COPM确保了每个人任务的相关性但是作为一个调查工具不是很有效。
许多IADL评估被设计用于中风患者,因为中风者可能有认知障碍。这些项目包括比如理财能力,记得服药的能力,使用电话的能力,这些或许可以反映这个障碍。
休闲和社会活动经常被包含在IADL评估中,有建议认为休闲应被作为社区生活整体满意度的一个指标。可是,由于休闲是如此复杂的一个领域,很难通过几个简单的指标来测量,独立的评估已经被建立比如诺丁汉休闲问卷,详细探索了这一领域。
综上所述,在对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测量上,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尽管通常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失能要看其是否能够执行ADL,但是应该选取哪一种测量量表作为标准呢?即使选择同一种量表,那么该量表内容是否达成一致,是固定不变的呢?第二,在量表内容的安排上,根据社会分工的差异(尽管男女平等),有些事情往往由女性完成,比如洗衣服,做饭,购物等,如果量表中这些项目所占比重较高,势必会影响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第三,因国情不同,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运用国外的问卷来测量国内老年人是否合适呢?要不要改进呢?若要改变量表,标准是什么呢?譬如在英国的老年人自理能力的测量中有的学者加入是否可以独自沏一杯茶呢?在中国对老年人依赖程度的测量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加入一些中国元素呢?
可见在对失能老人认定标准的精细化程度上是存在差异的。构建适宜中国国情的日常生活能力量表是必要的。